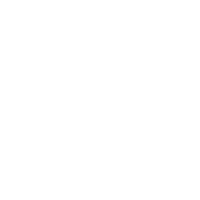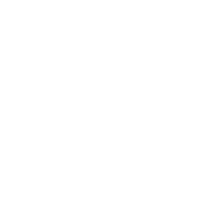五讲四美运动
 发布日期:2025-08-04
发布日期:2025-08-04  浏览量:
浏览量:
历史背景与时间节点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在新旧观念碰撞中面临新挑战:十年动乱对传统美德的冲击尚未完全消弭,部分群众中出现公共意识淡薄、言行失范等现象,与现代化建设所需的文明环境形成反差。在此背景下,重塑社会道德秩序、培育文明新风成为时代需求。
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倡议,在全国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 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响应,198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1983年又增加“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内容,形成“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完整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影响深远的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
事件概述与核心内容
五讲四美运动以群众性实践为特色,从日常生活细节切入,推动文明习惯的养成。在城市,街道社区组织“文明礼貌月”活动,志愿者走上街头维护交通秩序、清理环境卫生,商场、车站等窗口单位开展“语言美服务”,用“您好”“谢谢”“再见”替代生硬的指令性语言;在农村,村民们自发整治村容村貌,倡导“红白喜事简办”,抵制封建迷信与铺张浪费;在校园,学生们通过“文明班级”评比,践行“心灵美”——尊敬师长、互助友爱,让“行为美” 体现在不随地吐痰、不损坏公物等小事上。
其核心内容始终围绕 “人的文明化”展开:“五讲”侧重行为规范的外在约束,从公共秩序到个人品德,构建起清晰的行为准则;“四美”则深入精神层面,将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灵的美化相统一,既要求环境整洁、语言得体,更强调“心灵美”这一根本,即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道德观。二者相互支撑,共同指向“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的目标。
领导人论述
邓小平对这一运动给予了明确支持,他在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中指出:“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段话点明了运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定位,强调其对培育公民道德的实践价值。(出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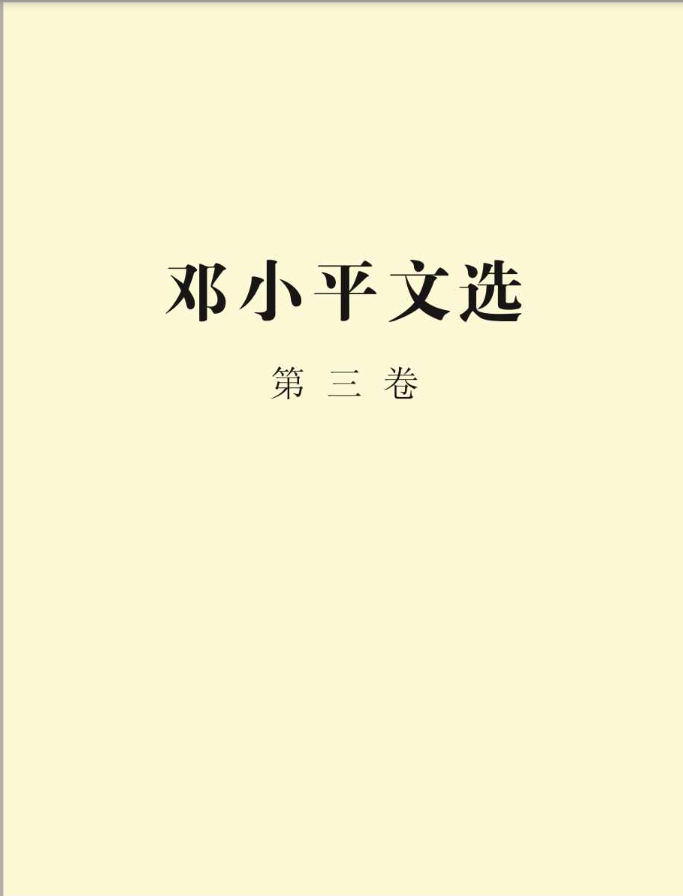
重要文件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首次明确提出“五讲四美”的概念与具体内容,呼吁“把文明礼貌活动普及到全体人民中去”,成为运动的起点(出处:《人民日报》,1981年2月26日刊发,第1版。)
1982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中强调正式将这一活动纳入全国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出“每年三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把‘五讲四美’活动同城市综合治理、农村“五讲四美”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活动从自发走向规范(出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5-12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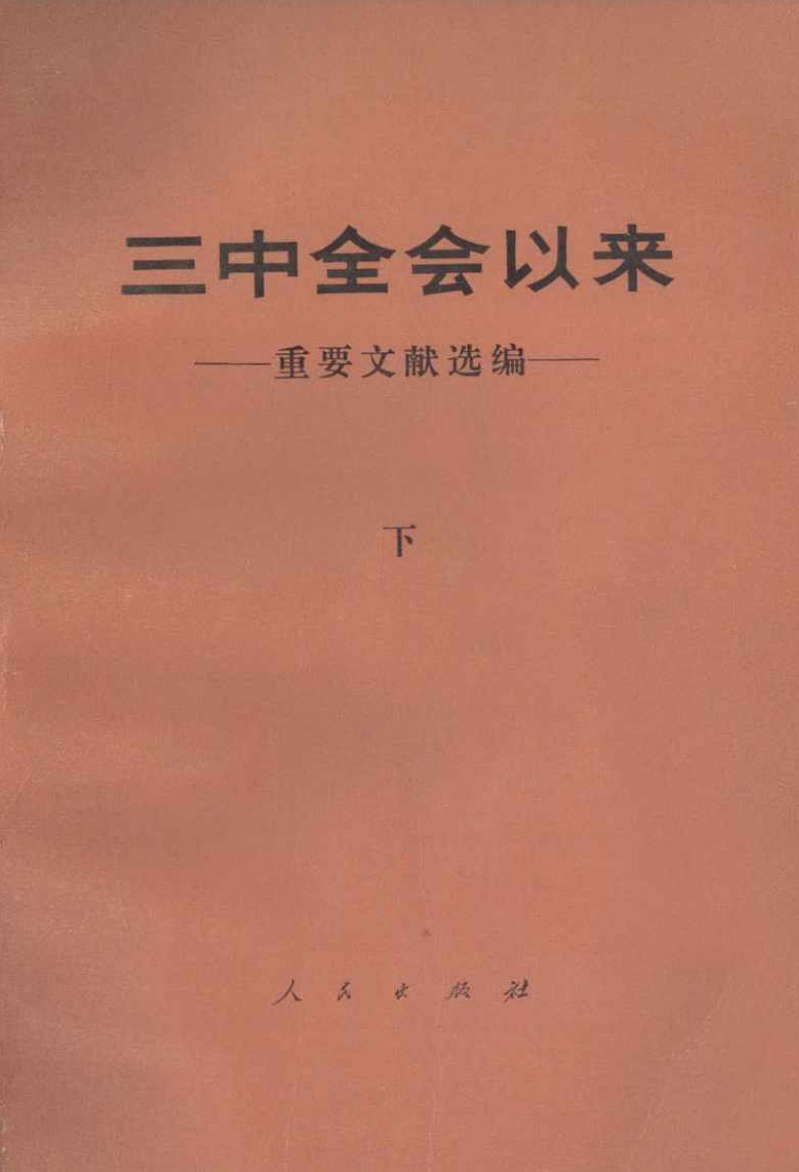
道德意义
五讲四美运动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注入了鲜明的道德记忆底色。那些关于“不随地吐痰”“排队候车”“说文明用语”的倡导,看似琐碎,却像一把把小刷子,一点点清扫着社会风气中的积尘,让“公共文明”从模糊的概念变成可感知的日常——这种对细节的规范,沉淀为集体记忆中“讲秩序”的道德共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公共行为。
“心灵美”与“行为美”的结合,则在记忆中种下“内外兼修”的道德种子。当人们回忆起“学雷锋、做五讲四美标兵”的口号,联想到的不仅是整洁的街道、礼貌的话语,更是对“做一个高尚的人”的向往,这种记忆让抽象的“道德”变得可触摸、可践行,为后续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从细节入手”的范本。
而“文明礼貌月”等形式的延续,让这种道德记忆获得了周期性唤醒的机制。尽管时代变迁,“五讲四美” 的表述或许不再频繁提及,但它所培育的公共意识、文明习惯,早已融入民族的道德基因,成为当人们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友善对待他人时,那份无需言说的默契与共识。
上一篇 : 抗洪精神
下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